(完) 他跪了三天三夜,才求得爹娘将本该嫁给他哥的我娶回了府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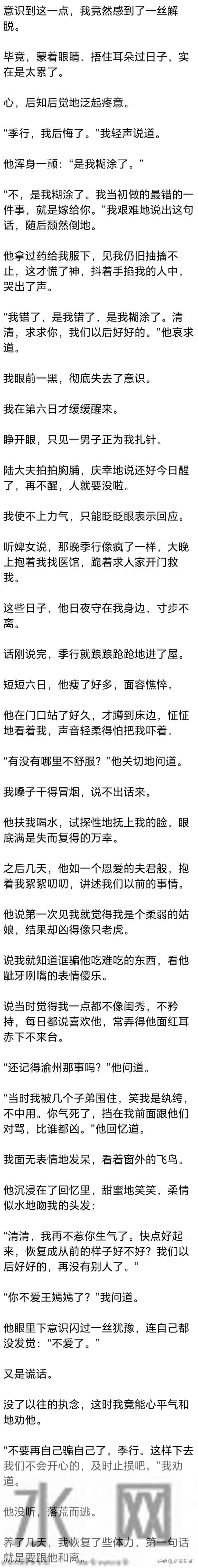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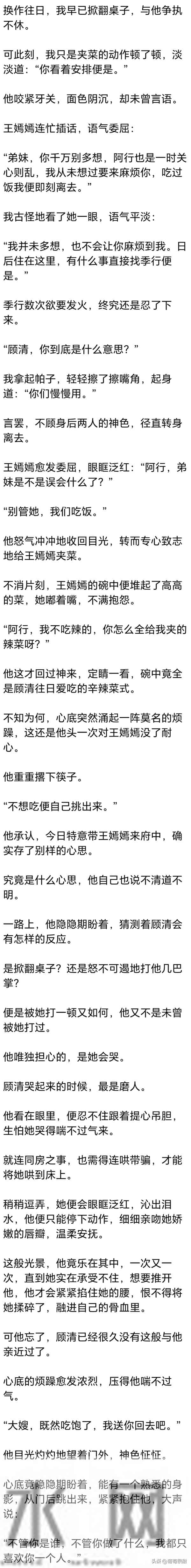

“姐姐,姐姐……”
他清俊的眉眼染上绯红,急切地咬住我的唇。
“姐姐,看着我。”
但年轻,便是最大的资本。
我在软榻间沉浮,一夜荒唐。
再睁眼时,身侧坐着一袭白蟒长袍的季行。
他坐在床沿,面色阴沉地盯着我。
“你的唇破了。”
我抚上唇瓣,痛得“嘶”了一声。
他脸色更沉:“怎么弄的?”
“不小心磕的。”
“在哪儿磕的?”他追问不休。
我困倦至极,懒得应付,便又阖上了眼。
合眼前,只瞥见他欲言又止的神情。
四周归于沉寂。
他该是走了。
将睡未睡之际,恍惚听见耳畔有低语。
“顾清,你起来同我吵一架,好不好?”
一只手抚上我的眉眼,带着痴缠。
“别不理我。”
这一觉睡得格外安稳。
醒来时,发现自己正枕着一个人的腿。
季行一手执着一束发玉带,一手轻抚我的发,神情难辨。
那发带,是陆容泽的。
他察觉到我的动静,低头看来。
“醒了?”
“饿不饿?”
他随手将玉带掷于地上,将我抱至圆桌旁。
桌上已摆好几道热菜。
他吻我的侧脸:“想吃哪道?”
我用力擦掉。
“我能自己吃,别抱着我。”
他神色一僵,终是笑了笑,松开我:“好。”
季行一直陪我到日暮。
我绣花,他便在一旁静读;我起身,他便负手相随。
他讨好地牵起我的手:“我告了几天假,只想好好陪你。”
我只好打消了出门取和离书的念头。
夜里,他立于衣柜前,望着里头的两个包裹发怔。
“为何把东西都收起来了?”
我疲惫地闭眼,编了个蹩脚的借口:“都是些不要的旧衣裳。”
他也不知信了没有,只得上床,从身后拥住我。
“睡吧。”
我挣扎了一下,他却抱得更紧。
他将脸埋在我的发间,长长叹息。
“顾清,我爱你。”
良久无言。
时间太久,我都忘了曾经有多渴望这句话。
可一切都太迟了。
我早已不屑一顾。
这几日,他寸步不离地守着我。
我被他软禁在府中,无论去哪,身后总跟着两个嬷嬷。
他遣散了下人,取出一对云蝶玉佩。
“看,这是什么?”
我认得,这是当年在渝州时,我赠他的定情信物,一人一枚。
他从未佩戴过。
后来,又当着我的面摔得粉碎。
他笑着将属于我的那枚放在我掌心。
“我寻了许多店铺,才找到一位老师傅,费了好大功夫才修复如初。”
玉佩温润通透,一如当年。
我手一松。
他脸色骤变,慌忙在半空接住,紧紧捂在心口。
我摊开手:“给我。”
他面色惨白:“别摔它。”
“给我。”
他仓皇摇头:“我求你。”
“不给也行,那你放我走。”
他沉默了。
我嗤笑:“不是说爱我?你就是这么爱的?什么都不肯给,算什么?”
他张了张嘴,终是妥协:
“我给你别的玉,你想摔多少就摔多少。”
“但这毕竟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”
我看着他,一字一句,斩断过往。
“假的,这是你骗来的,我们的情意也是假的。”
“这玉佩,本是要给你大哥的。”
他猛地抬头。
“你胡说!你说过无论我是谁,你都喜欢的,你明明叫的是我的名字!”
“你亲口说的,为何不认?”
他眼眶泛红,急切地想来牵我,却被我甩开。
我疲惫地叹气,不知为何,我们总会走到这般地步。
“季行,别再互相折磨了。”
5
我绕至后院一侧,瞧见一名佩刀侍卫单膝跪在季行身前。
季行漫不经心地抛出一条发带。
“还没寻到人?”
“属下无能,未能找到。”
他发出一声怪异的笑声。
“罢了,再宽限你两日,寻到之后,直接了结。”
我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,刹那间,浑身血液仿佛凝固。
身旁的嬷嬷轻声唤他:“大人。”
季行目光转来,幽深似渊,仿若鬼魅。
他腰间一枚云蝶玉佩,莹润剔透。
“怎的出来了?”
他双手将我打横抱起,送我回到屋内。
季行好似疯魔了。
他在我房门处落了锁,还派人守在外面。
我彻底失去自由,只能等他下朝归来,才能透过门缝瞧瞧屋外的景致。
“说你爱我。”
他用力钳住我的脸:“说你爱我,我便不杀他。”
我满眼恨意地瞪着他,被他一只手遮住双眼。
“你曾劝我莫要犯傻,莫要将心爱之人拱手让人,我自然听你的,将你锁在我身旁。”
“怎么样,我乖不乖?”
黑暗里,他的唇瓣轻轻吮住我的。
明明被困的是我,绝望的却是他。
一滴咸涩的泪滑入我口中。
“清清,你恨我吧。”
不知浑浑噩噩过了多久,季行一连两日都未出现。
屋外的嬷嬷也不知去了何处。
我心中狂跳,趴在门前,鬼鬼祟祟地听了许久,而后用力踢开了门。
府中空荡荡的,不见一人,我赶忙收拾了包裹,从小门离开。
一路毫无阻碍。
没走几步,巷子里倒在血泊中的陆容泽让我脸色瞬间煞白。
所幸,他只是腹部受了伤,尚有意识。
他拿出一张纸,向我邀功:“和离书。”
“我已安排好船只,别怕,季行不会再来了。”
“还有,”他嘟嘟囔囔道,“带上我一起走,别丢下我。”
我搀扶起他。
“别说话了,能撑住吗?”
他已是进气少出气多的状态,却强撑着笑了笑。
“嗯。”
上了船,我为陆容泽包扎好伤口,这才松了口气。
大船缓缓离岸。
远处传来马的嘶鸣声,季行骑马疾驰而来。
我忍不住瞳孔一缩。
他在岸边,静静地与我对视。
不过两日未见,他便消瘦了许多。
相隔太远,只能看到他张嘴,说了些什么。
他深深看了我一眼,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,坠下马去,背后被血浸透的衣衫一闪而过。
我不愿再看,收回视线,照顾昏迷过去的陆容泽。
脑海中浮现出他说的那句话。
“求求你别走。”
“顾娘子,你这帕子的针脚走线着实精细,我再订五条。”
“嗯,行嘞!”
陆容泽刚出完诊回来,轻轻捏捏我的肩膀。
“累不累?”
秦大娘捂着嘴直乐:“哎哟,羞死个人啦,行啦,我就不在这儿碍你们的事儿了,等几日我再过来啊。”
陆容泽笑眯眯地回应:“秦大娘慢走。”
等人离开,他抱着我亲了一口。
“有没有想我?”
“一般般吧。”
他不满意地挑起眉毛:“那可不行,我想你想得都差点摔个跟头,你居然只是一般般?”
“不公平!”
他愤愤地咬上我的肩膀。
“嘶,属狗的呀,天天咬人?”
他在我身上乱蹭:“娘子,娘子好不好嘛?”
我看他耍无赖就头疼得厉害,推开他:“不行,腰好酸。”
“那我给你揉揉。”
我闭着眼睛,在他肩头寻了个舒服的位置,不一会儿就睡了过去。
自我与陆容泽来到这个依山傍水的小镇后,便靠卖帕子维持生计。
当初逃走时,他告诉我,他看到我府外有许多人把守,便知事情不妙。
许久联系不上我,他便求到了自己父亲面前。
镇西王醉酒后与婢女厮混,稀里糊涂有了他。
他娘生下他后,被赐了一杯毒酒,香消玉殒。
他也被亲爹厌弃,扔给奶娘照看便不再管。
府里下人见他不受宠,动不动就苛待他。
在他十岁那年,他拜了一位江湖郎中为师,终于逃出了那座如炼狱般的府邸。
他长大后,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爹,便是因为我。
镇西王答应了他的请求,前提是斩断亲缘。
“所以姐姐,”他赖在我身上不肯起身,“你一定要带上我,不然我就无家可归了。”
季行那日背后的伤,是受家法惩处所致。
得罪了镇王府,老夫人为了保全一家老小,只得对他施以家法。
可季行直到背后血肉模糊昏死过去,也未吐露一个字。
我与陆容泽成了亲。
陆容泽拿出半辈子的积蓄,请了全镇的人来观礼。
这次的成婚夜,新婚夫君十分温顺。
乖乖与我喝合卺酒,乖乖帮我卸下厚重的钗环。
满屋喜色,他的眼睛被映衬得格外明亮,嘴角一直上扬。
他褪下衣衫,不好意思看我,说的话却带着几分勾人。
“我今晚整个人都是娘子的。”
后来发现,不是今晚,是每晚皆是如此。
他从起初的羞涩,到后来的食髓知味。
我被他缠得烦了,一巴掌挥过去,被他不要脸地拉到身下,坏笑着说:
“娘子帮帮我。”
我已经很久没犯过哮病了。
他日日帮我调理身体,不让我做重活,每日陪我到路边散步。
我没想到能再次见到季行。
陆容泽硬要拉着我走,让我没病走两步。
我走累了,便撒娇让他去给我买串糖葫芦。
他无可奈何地凶了我一眼,我得逞转头,见季行立在风中。
柳叶在他身后随风摇曳,他的神色着实不太好。
这处虽是小镇,多少还是能听到上京的消息。
听闻季府已然衰败,一蹶不振,一家老小的开销全靠季行一人支撑。
他如今衣着朴素,只腰间固执地佩着一枚品相极佳的蝶样玉佩。
陆容泽此时买好一串糖葫芦过来了,要跟我比试,看谁先到家门口,谁就能吃。
我心头的愁绪刚起,就被他这要求冲淡了。
因为陆容泽这家伙不要脸,他是真的会吃。
我如临大敌,完全忘了身后的季行。
陆容泽跟在我身后,笑着叹了一口气,牵起我的手。
“别走这么快,往后的路我们一起走。”
我斜他一眼:“那这糖葫芦是你吃还是我吃?”
他抿嘴坏笑:“我有更好的吃法,要不要回家试试?”
不经意转头,季行已经离开了。
度过严寒,接着便是春日。
此时正值开春,万事万物都散发着新生的气息。
我与陆容泽携手,在江边漫步。
柳树枝条轻轻拂在手上,满目皆是春光。
完结

本文标题:(完) 他跪了三天三夜,才求得爹娘将本该嫁给他哥的我娶回了府
本文链接:http://www.hniuzsjy.cn/shenghuo/4567.html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






